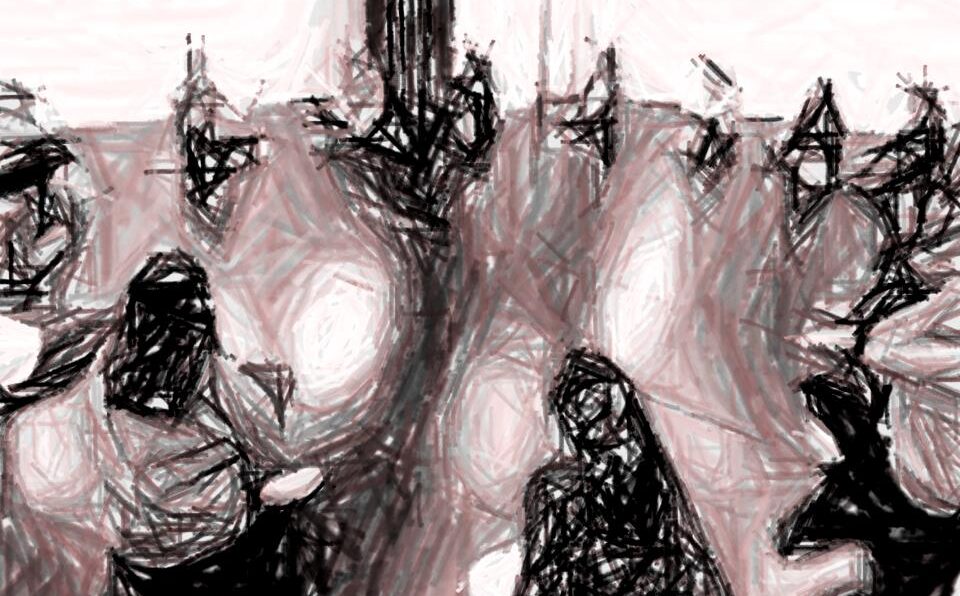|
| 人物:溫吉興 攝影:王弼正 |
文字:吳思鋒
1993年,臨界點劇象錄劇團藝術總監田啟元,編導了後來奉為經典的《白水》,溫吉興飾演白蛇。他說,他其實不知道當時自己在演什麼,但又看到觀眾很能夠接受這個角色。可以說,回頭數算這21年來的劇場生活,他都是為了要搞清楚那時候「為什麼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」。
時序拉回與《白水》同年,不過較早上演的《平方》。他以往的話劇概念在那一回被顛覆;舞台上沒有景片、沙發或者任何寫實的道具,異常簡約。「演員只穿小白短褲,舞台幾乎沒有佈景或多餘的東西,用非常緩慢的速度在移動……」溫吉興這麼敘述他被「嚇到」的啟蒙經驗。那時身為工作人員的他,還趁著大家去吃午餐時走上舞台,像演員一樣慢速行走,結果沒有三四步就晃倒,讓他驚覺「哇塞!原來這是需要身體訓練的」。
於是他加入臨界點,開始漫長的劇場之路,這條路上撇不開營運已然停擺的臨界點,劃不掉1996年去世的田啟元。退伍後曾給自己三個未來選項的他,最後仍然「選擇」劇場。
從田啟元過世到志同道合劇展
田啟元去世的那一年,也是溫吉興入伍的第一年。他說:「等到我退伍前有比較多假的時候,每個禮拜放假幾乎都是回臨界點,不是回家,可是臨界點已經沒有人了,我一個人坐在空空的排練場,一整個下午,沒有一個人。」
退伍後,他回到臨界點,與雷若豪等人籌備志同道合劇展,打定主意一個月演一齣戲,也藉機把當時臨界點瀰漫的悲傷氣氛洗掉。「因為我不喜歡人家說,臨界點樹倒猢猻散。」他說。
第一份企劃書,不會用電腦的他花了兩週才一字一字敲完,但到第一次拿到補助(六萬元),已經是送到第六份企劃書的時候了。接下來好幾年,臨界點經歷了一段異常熱鬧的時期,從最初三五個人固執地每個月創作一齣戲,到後來有六七十人來來去去,補助也愈來愈多。這時候,溫吉興卻覺得累了,便將行政工作交接給團長詹慧玲。離開臨界點後的一年半之內,他連續接了十六齣戲,「也是想趁此忘掉什麼吧」他說。
2006年,臨界點在民樂街的空間正式結束營運,溫吉興一個人住在東區的頂樓加蓋,起初沒有戲可以接,後來才開始接觸影像拍攝,慢慢可以養活自己。逐漸穩定以後,他搬到新店的公寓,除了演戲之外,過著每週只玩牌、打棒球、上教會」,退休般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他發現「慘了」,「慘」的原因是,他覺得自己的「心」不在劇場了。
 |
| 攝影:王弼正 |
拉臨界點成員下水,成立小劇場學校
多年來,有許多他口中的「小朋友」(18 ~ 40歲都有),總是在演出後請他提供表演上的意見,他常常講到對方哭。溫吉興覺得他們難過的是,他們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學,因為這樣才有可能在舞台上把表演「做完」。
看到這樣的空缺似乎是被需要的,溫吉興說:「我能給嘛,我也什麼都沒有,能給的也就這些」。他便把張吉米、王瑋廉、林文尹、李建隆等,以前臨界點的成員拉下水,掛牌成立小劇場學校。
溫吉興說:「我也不覺得應該要上了課才能做表演,可是光台北市就有幾百個團,導演在兩三個月內要排戲又要教表演,是不可能的。演出是很消耗的事情,如果演員在當中沒有學習到事情,經歷就是空白的,因為表演是要累積的。」
小劇場學校最早只是一期三個月的課程,透過臉書宣傳招來十名學生,其中有五位是曾被他批評過的;結束後,同一批人接著進行第二期課程,就這樣到現在,已經擴充為一到三年級,加起來有數十人的師生規模。課程規劃上,一年級有七、八位老師帶身體訓練,一週兩堂,一年下來將近一百堂。二年級是多元課程,內容包括書法、哲學、紀錄片等;三年級不上課,而是寫計畫書,去做展覽規劃、演出、創作都好,同時找一位指導老師。
這些看似長遠的規劃,原先並不在溫吉興的預料之內,可是學生就一直透過口耳相傳報名、徵選進來,有些是科班,更多是來自各行各業,想要上台表演的人們。他不會自我膨脹地以為這真的是間學校,也自認無法給學生一個表演「系統」。他能做的,就是盡量提供各式各樣的課程,重點擺在「傳承」,讓學生透過與擁有十幾年經驗的講師共度課堂,不僅學習他們的劇場技術,也體會他們對劇場的態度。
演員的自覺
「我常常跟學員講我是怎樣準備演員的工作。演《陽台》(2004)時,我每天早上用餐後開始讀劇本,每天讀,下午花三、四個小時,起碼看著劇本唸十遍、二十遍,晚上排戲,然後做筆記,回家洗澡睡覺,隔天重覆,維持兩三個月。」
〈演員的準備〉、〈角色的建立與卸下〉……這些溫吉興於2004到2011年間發表於部落格「劇場猩猩」,累積近200篇的筆記所反照出的「演員自覺」,幾乎都濃縮在前面那段話了。「我不覺得我在吹牛,也不是炫耀。每次跟他們講,我可以從他們眼神看到,他們也想這麼做。但現在的小劇場已經不可能這樣了。」他說。語氣逐漸轉弱。
 |
| 攝影:王弼正 |
11月初某一晚,我從牯嶺街小劇場外圍階梯上二樓,預備看戲。有個人正用黑色垃圾袋黏成一大片遮雨棚,抬頭一看,原來是溫吉興。他抵著細雨,填補某種空缺似地為學生的製作而工作著。這位在訪談時說了好幾次「我能給的也就這些」的劇場演員,這麼多年來,其實已經做了很多,很多。
本文刊於表演藝術雜誌